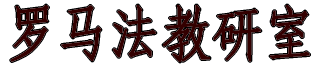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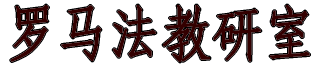

| 本站首页 La prima pagina di questo sito |
罗马法原始文献 Le fonti del diritto romano |
罗马法论文 Articoli del diritto romano |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 Diritto romano e diritto civile moderno |
法律拉丁语 Lingua latina giuridica |
|
|
|
对民法的哲学诠释的思考 ——以徐国栋教授的研究为个案的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关于中国民法典的起草思路的争论中,徐国栋教授主持设计的民法典草案在编的层次设计上分为人身关系法和财产关系法两部分。徐教授认为,在编的层次上作如此设计的一个理论渊源是哲学上的精神与物质相对立或主体与客体的相对立的理论(该理论属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范畴)。[1]他进而认为:“如果仔细观察,可发现民法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极为一致,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这是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式的思考确立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二元论的成果。人法与物法的二分,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二分的法律化。”[2]显然,这是徐教授在对依据自己的研究思路所划定的,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中所须解决的认识论、价值论、人性论等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之后,对民法典草案中的具体设计在编的层次上所作的最新的哲学诠释。本文就拟以徐教授对其民法典草案中编的层次之设计的哲学诠释为个案,以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的相应观点为视角,就民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中的诠释方法作一些初步思考。下面首先对相关概念作出交待,以更清楚地阐明本文的主题。 本文中的“诠释”范畴,既是在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诠释学中的概念,也具有哲学诠释学中“诠释”所具有的一些内涵。[3]在前者中,“诠释”作为一种“理解”,是人文科学的一种独特的方法。依照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观点,自然科学是从外部“说明”世界的可实证的和可认识的所与,而人文科学则是从内部“理解”世界的精神生命,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过去精神或生命的客观化物,而理解就是通过精神的客观化物去重新体验过去的精神和生命。[4]而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诠释则是理解、解释和应用的统一。理解离不开解释,解释是理解本身的实现,因为一切解释都具有语言,理解只有在解释的语言性是才能实现。而这里的“应用”乃是理解本身必具的成份,乃是把普遍的原则、道理即真理内容运用于诠释者当前的具体情况(但应用并非某种一成不变的原理或规则对任何具体情况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运用,相反,对具体情况的应用乃是对一般原理或规划的修正和补充)。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使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5]既然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本文的意义”进行诠释,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显然也离不开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诠释。[6]因而本文所称的“民法的哲学诠释”就是指在民法基本理论领域运用哲学这一工具性学科的理论对民法制度所作的理解(或诠释),是一种“关于民法的理论”;而并非旨在解释具体法律规范或运用法律规范进行裁判的具体的法律诠释,这乃是一种“根据民法的思考”。[7]“关于民法的思考”的思维方式强调从多维视角出发,运用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体系,综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民法现象。而“根据民法的思考”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从现行民事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态出发,运用逻辑的、经验的方法,解释民法的存在形式和内容。因此徐国栋教授运用哲学工具对民法现象的诠释(理解)显然就是一种“关于民法的理论”。进一步,徐教授关于民法的哲学诠释的合理性问题——也即徐教授将哲学理论作为研究民法基本理论的一种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每一次运用是否都达到了理论上的自洽——就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民法的哲学诠释的合理性标准何在? 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诠释学从它原来与神学、语文学的独断论的联系中解脱出来,并发展成一门关于文本理解、人理解或历史事件理解的普遍学说,对象领域的扩大必须使诠释学失去它与某种特定文本的必然联系,也失去它与真理的特殊关系。因而这种诠释学的任务不再是使我们接近特定的真理,而是发展避免误读文本的技术。[8]而伽达默尔认为其所创立的哲学诠释学的“任务根本不是要发展一种理解的程序,而是要澄清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完全不具有这样一种‘程序’的或方法论的性质,以致作为解释者的我们可以对它们随意地加以应用——这些条件其实必须是被给予的。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和前理解,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9]可见,上述两种诠释学并没有涉及诠释(理解)的客观性、合理性标准的问题。更有甚者,伽达默尔强调只要存在理解,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他要求诠释者在规范性问题的理解中,思考多种理解世界的差异。理解不是对对象的客观性的理解。这样,他实际是等于放弃了正确诠释的标准。[10]因此,哲学诠释学对法律诠释的客观性提出了挑战,而法学家则对维护法律及其诠释的客观性进行了不懈努力。[11]如有学者指出,某一特定主体对法律的理解与诠释是否构成真正的理解,需要客观性制约。客观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合法性。如果诠释结果与法律文本所设定的规范意志一致,这样的诠释就是客观性的。如果诠释结果悖离法律的规范意志,表现出诠释的任意性或完全的个人化,就不能被视为客观性的诠释。二是诠释共同体的认可,即在职业群体中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在此共识基础上,法官理解法律、解决纠纷寻找出来的是可以接受的答案。[12]笔者认为,这种法律诠释的客观性标准,侧重适用于旨在具体适用法律时的诠释活动,是“根据法律的思考”这种思维活动的一种指导准则。而民法的哲学诠释作为“关于民法的理论”,这种诠释的合理性标准,就应有其特殊的规定性。 葛洪义教授在分析法理学学科作为一门科学的界限时指出,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意义上的法理学理论。至少有以下三项标准:(1)是否由一个法律领域的“真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统率性的逻辑前提。该问题的真假取决于四个方面:①是否属于一个法律问题;②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的理论问题;③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④该问题是否有助于法理学的进步和发展。(2)是否能清楚地标示出该法理学理论所属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脉络(因为法理学理论不可能离开后者而存在,相反,它必须借助这些理论来阐明自身的内容)。(3)是否能将一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还原为、凝结为法律理论。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门类的“合法性”的根据,就在于法学需要与各个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或知识进行交流、对话。[13]笔者以为,上述三项标准同样也是判断一种法理学理论(也即一具体的“关于法律的理论”)是否具有“合法性”(即 Legitimacy,也可译为“正当性”)依据的标准。进一步看,因为法理学乃是其它法学学科的“元理论”,其判定一具体的“关于法律的理论”的“合法性”的标准同样适用于其它法学学科中“关于某种法律的理论”的研究上。所以,民法的哲学诠释作为一种“关于民法的理论”,判断某一诠释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也就至少是上述三项标准的民法化(表述上,只要把上述三项标准中的“法理学理论”、“法律理论”等概念换成“民法理论”即可)。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在具体适用法律以裁判案件的场合,法律诠释的正当性主要体现为“客观性”,因为虽然法律诠释共同体对诠释结果也难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法官必须当下作出诠释,并且该诠释是符合法治原则下的合法性标准的客观性诠释时,才有说服力。[14]这种“客观性”出于法治原则和依法当下裁判案件的情势的要求。这也是“依据法律的思考”中对法律诠释的必然要求。但在“关于法律的理论”中,我们却是依据其他学科的思想和知识来理解法律,此时的法律诠释所应具有的“正当性”,就很难以合乎法律规范这种意义上的“客观性”来概括了,而应以合乎理论逻辑的自洽这种意义上的“合理性”一词来概括。这也就是本文中保留其他学者的“法律诠释的客观性(标准)”,这种提法和提出“民法哲学诠释的合理性标准”这一表述的原因。第二,尽管在法律的具体适用和法学理论研究中,两种法律诠释的正当性标准不尽相同,但它们还是有共性的。比如,前述法律诠释的客观性标准中的“合法性”一项,就是用以评判上述“关于法律的理论”中诠释合理性标准的第一项“是否由一个法律理论领域的真问题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依据;而前者中的“诠释共同体的认可”也是用以判断后者中的“(研究前提)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和“是否能将其它学科的理论还原为法律理论”的一个基本途径。第三,这种判断“关于法律的理论”的诠释合理性的标准仅仅是相对意义上的标准,仅是宏观的、抽象的指导准则,并不具有可以对任何诠释当下作出恰当判断的作用。根据波普尔的说法,为保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与其求诸科学家的态度,不如求诸科学社会活动的公共性格。我们可以将公共性格间的互为主观讨论、批判看成保障社会科学寻求客观性的工具。[15]因而,针对具体的诠释,我们应依据上述三项标准,并且展开学术讨论、批判来判定该诠释的合理性。以下,本文就试图参照上述标准对徐国栋教授关于民法的哲学诠释作一些评价。 三、民法典草案设计的“哲学依据”:一项“过度的诠释” 徐教授在《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一文中,将其草案中编的层次之设计的理论渊源首先归结为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确立下来的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三编制体系。徐教授同时认为,在这种三编制中,“人法与物法的对立以人与物的对立为基础,……翻译成哲学语言,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或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他还以西塞罗说过的——“为了理解词并为了写作,没有什么比做把词划分为两个种更有用和更令人愉快的练习了:一个种是关于物的,另一个种是关于人的”——作为上述对立为罗马法学家所熟知的例证。在《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一文中,徐教授更明确地指出:“民法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极为一致,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人法与物法的二分,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二分的法律化。”“人文主义的民法——大陆法系的所有民法,除了德国法族的以外,都属于这一类型——认为主体是第一性的,客体是第二性的,因为人是这个世界的出发点……外在的物质世界存在于与人的关系中,是人化了的。但人在走向外部世界开展各种活动之前,首先得整理自己……这种整理的成果就是所谓人法,物法是人的意志投射于外部世界的表现,是人的活动作用于此等世界的结果。”[16]针对徐教授关于《法学阶梯》和现代民法的哲学诠释,本文先从法学和哲学方面进行分析,然后再运用哲学诠释学的相应观点作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根据学者的分析,《法学阶梯》中虽然存在纯粹的主体法意义上的“人法”,但该“人法”并非内容完整的人身关系法。因为由优士丁尼进行的法典编纂的成果包括《法学阶梯》、《学说汇纂》和《敕令汇编》,3本书的总和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典。因而《法学阶梯》及其“人法”就不是完整的罗马法法典文本。其次,从《法学阶梯》的结构来看,作为一个家庭代表的自权人家父才是完全的法律意义上的人,其他的家内人都不享有这种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家父为代表的家庭可视为是主体。这种法律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家族主义制度,法律适用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所以此“主体”并非哲学乃至现代民法意义上的作为自然人的彼“主体”。再次,《法学阶梯》的物法中的“物”还包括了无体物(如继承权、债权)的概念。这样的“物”是一种法律关系,与哲学上的客体概念没有联系。所以,《法学阶梯》体系作为一个并不完整的罗马法文本,并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出只是在近代才被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理念。 其次,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的论断非常明确:“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表明哲学不是以“思维”和“存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关于“思维”和“存在”的某种知识,而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来研究。再者,不能把哲学基本问题简单、直接地归结为或等同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何为本原、何为派生、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的“时间先在性”问题。在“时间先在性”的意义上,精神和物质的对立是僵硬的,其先后顺序并不能颠倒,即物质先于精神;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而“存在”这个范畴不等于“物质”范畴,用近代哲学的方式说,“存在”不仅是“意识外的存在”(即客观“物质”),而且是“意识界的存在”。同样“思维”范畴不同于“精神”或“意识”,在近代哲学的意义上,“思维”不仅指“意识的内容”,而且指“意识的形式”;不仅指关于思维对象的“对象意识”,而且指构成、把握和反省“对象意识”的“自我意识”;不仅指“思想的内容”,而且指“思想的活动”。[18] 近代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存在”是“意识外的存在”,即是客观实在的“物质”的存在;其理解的“思维”则是“意识界的存在”,即作为“意识内容”的存在。所以近代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实质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意识内容”与“意识对象”的关系。而近代唯心主义所理解的“存在”是“意识界的存在”,即“意识内容”;其所理解的“思维”是把握和统摄“意识内容”的“思维活动”,而非近代唯物主义理解的“意识内容”。所以近代唯心主义所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思维活动与“意识内容”(即“意识界的存在”)的关系。[19] 由上可知,徐国栋教授首先是在近代唯物主义的视野内理解哲学基本问题,所以这种“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本身就具有一定局限性。其次,他把现代民法制度的两大部分——人法(实为人身关系法)和物法(实为财产关系法)——二者在民法典中的顺序关系作为近代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来思考,因此就把物法先于人法的这种民法典结构的一个理论根源归功于马克思的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实践唯物主义。[20]这里就存在着理论上的过分“化约”和论证上的“断裂”。第一,民法上的“人法”本是主体法的意思,然而在与“物法”相对应而作为民法典内容的半壁江山时,此“人法”实为“人身关系法”这就无形中造成了概念的偷换。第二,即使在本来的意义上,“人法”作为主体法,它也很难用近代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精神”(即“意识内容”)来加以诠释。而“物法”作为财产关系法,本身乃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财产利益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则更无法与近代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作为“意识外的存在”的“物质”相提并论。第三,既然“人法”与“物法”都有民法理论上的固有内涵而无法化约为哲学(尤其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精神”与“物质”范畴,那么“人法”与“物法”在民法典中的不同顺序就与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论形态无关。既然财产关系法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财产利益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制度),那么所谓“物文主义”的民法典编排体系(也就是物法先于人法的民法典设计)当然也能理解为是对人在与财产利益有关的民事活动(实践)领域的重视(而对人在与其人格利益、身份关系有关的民事活动(实践)领域则相对轻视),所以这种民法典(包括其物法)的哲学意蕴当然也是“一种以实践——即主动者主体作用于受动者客体的活动——为中介观察人与客体的关系的思想”(徐教授以这种说法来概括为“物文主义”民法典所缺乏的哲学理念),而并非是与人(主体)的能动性、目的性无关的“客体第一性”的思想。[21]所以,徐教授针对其民法典草案中编的层次之设计所作的哲学诠释,没有将近代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哲学基本问题还原为、凝结为民法基本理论,不符合“关于民法的理论”的诠释合理性标准中的第三项,是一种“过度的诠释”。[22] 那么,这样一种“过度的诠释”又是怎样一种过程呢?本文就拟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去“描述”一二。 伽达默尔提出的“完全性的前把握或前概念”意指“只有那种实际上表现某种意义完全统一性的东西才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当我们阅读一段文本时,我们总是遵循这个完全性的前提条件,并且只有当这个前提条件被证明为不充分时,即文本是不可理解时,我们才对传承物发生怀疑,并试图发现以什么方式才能补救。”因此我们对文本的解释是必然由一种完全性的前把握或前概念所指导的,这种完全性的前把握是我们前理解的一部分,它是我们一般理解文本的必然条件。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支配我们理解的完全性前把握不仅预先假定了一种内在的意义统一性来指导读者,而且读者的理解也经常地由先验的意义预期所引导,而这种先验的意义预期来自于与被意指东西的真理关系。因此,前理解的完全性前把握是我们阅读的经常陪伴者,通过这种前把握,我们排除那种把文本作为矛盾、不可信或直接错误来看的阅读方式。以这种阅读方式,我们试图这样解释文本,即这文本首先更好满足于我们前理解地追求一个完美性文本的理解,并解释有关事情直到完美性。完全性的前把握事实上说明理解就是筹划,理解所筹划的东西就是先行于文本的期待。伽达默尔说:“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就部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预先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文本。”[23] 依据上述观点,笔者以为,存在于徐国栋教授的前理解中的一个“完全性前把握”就是他运用哲学诠释民法理论的认知旨趣。这种认知旨趣使他怀有在既有的法律文本中发现某种更为基本的“理念”的期待,而这种基本的“理念”就与他所偏好的并运用的哲学工具结下了不解之缘。基于此,尽管《法学阶梯》是不完整的罗马法文本(尤其在人法部分),但徐教授“排除那种把文本作为矛盾、不可信或直接错误来看的阅读方式”,从中“读出”了体现着哲学基本问题的“信息”。而这种近代的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哲学基本问题——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本身包含本体论(精神与物质谁为第一性)和认识论(精神能否认识物质的问题)两方的问题。[24]徐教授对《法学阶梯》体系的诠释对这两方面均有涉及:在本体论问题上,他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将财产关系作为民法首要调整对象(因而民法典中物法先于人法)的哲学方面的原因时,认为既然人—物的二分在哲学上是精神与物质的二分,因而法学阶梯体系在社会主义国家看来“是唯心主义的”(即人法在前体现了精神的第一性)。在认识论问题上,他认为人法与物性所体现的人与物的关系中涉及人与物的认识关系,也存在于三编制里的“讼”之中,在古罗马,人们常用宣誓决讼的方法来解决疑案的事实问题,这实际上表明三编制的司法的不可知论。[25]这就表明徐教授试图这样解释《法学阶梯》这一文本,即这文本首先更好地满足于他前理解地追求一个完美文本(这个完美文本即为他认为的完整涵盖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法律文本)的理解,并解释有关事情(这有关事情即为他认定的法律文本体现的哲学基本问题)直到完美性。尽管从民法理论和哲学理论看来,徐教授对《法学阶梯》的上述诠释中,在“人法”—“主体”—“精神”—“案件当事人”与“物法”—“客体”—“物质”—“案件事实”这两组概念里,每组四个概念之间的“同化”与不加论证的相互代替,就使得他将法学阶梯体系和近代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的哲学基本问题相互贯通的论点不具备立论的基础。另外,徐教授援引西塞罗“把词分为两个种”以利于理解和写作的说法来证明古罗马法学家熟悉哲学意义上的人与物的对立,似乎也是“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文本”的结果。起码这一例证对其论点并不具有很强的证明力。 四、诠释的方法:一种实践能力 上面的“描述”(或者在作为普遍方法论的诠释学意义上,是对徐教授的相关诠释过程的模仿或再体验)并不是分析徐教授对其民法典草案中编的层次设计的哲学诠释这一“过度的诠释”的原因,也不是力图寻找如何运用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关于民法的诠释”的合理标准,只是试图再现在一个具体的诠释中,作者的完全性前把握与一个法律文本“相遇”的过程。在哲学诠释学看来,为了根本理解文本,我们必须通过前理解构造一个意义整体,只有根据这个意义整体我们才能评判文本,因而这个以前是存在于文本自身之中的意义整体现在与前理解的完全性前把握相符合,只有根据这种意义整体的前概念,我们才能与文本相遇并借助某个完全性文本的理想解释文本。[25]这样,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进行“关于法律的理论”的诠释时,该理论工具就是法律文本的理解者的前理解中的意义整体(或曰“完全性前把握”)。所以,一次具体诠释的合理与否,只能在每一个前理解的意义整体与具体法律问题的“相遇”时的具体情境中,参照“关于法律的理论”的诠释合理性的标准,判断该诠释能否使其它的理论“还原为、凝结为”法律理论,能否使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互转化不致破坏每一种理论固有的逻辑自洽。因此,每一次的诠释总是面临着不同的“诠释学境遇”,总是需要具体地分析它的合理性。如徐国栋教授此前运用认识论诠释民法典的涵盖范围、法律渊源体制设计等问题,运用性善论性、恶论性以及经济人假设诠释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主体行为标准问题,都是成功的对于民法的哲学诠释。[27]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所运用的哲学理论这种“完全性的前把握”合理地还原为、凝结为了民法理论。 因此,本文仅仅试图结合徐国栋教授的一项具体研究,在民法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层面说明“诠释”方法的内在规定性,并介绍法理学界的观点作为判断具体“诠释”的合理性的初步标准。最后的结论也许是一个老生常谈,但笔者相信这是本文在经过一番“诠释”之后顺理成章得出的结果:要通过对法律理论的不同诠释(理解)以推动法学的发展,只有靠作为理解者的学者个人的严密、细致的论证与学术共同体的充分、认真的讨论。 注 释 [1]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载于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版,第63页。 [2]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于上注书,第145页。 [3]作为普遍方法论的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是关于诠释学的发展历史的两种不同描述和不同倾向。按照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尔的观点,诠释学的现代历史应由上述两种诠释学倾向所支配。与前一种倾向相比,后一种倾向更为重要,因为诠释学从局部性到普遍性的这种发展,只有当它使其严格的认识论倾向从属于它的存在论倾向时,才能最后完成。参见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以下。因此,出于论证的需要,本文中“诠释”概念的内涵包括了这一概念在上述两种倾向的诠释学学科中的相关内容,也是有理论依据的。 [4]、[5]见前引洪汉鼎书,第24页,第6—7页,第238页。 [6]葛洪义:《法律的理论与方法——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条件和界限》,载于其著《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7]葛洪义教授认为,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与其他法律法学领域相比,首要区别在于思维形式上:法理学的思考形式主要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而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者则主要是“根据法律的思考。”这两种思维形式本来是互补的关系,但现在由于学术分工带来的学科划分使得这两种思维形式被割裂开来,使得有人误认为法理学或理论法学以理论研究为中心,而其他法学学科、特别是部门法学,理论性至少不很重要。但这种认识并不正确。因为缺乏理论内涵的东西不可能在“科学”的层面上存在。见上注葛洪义书,第357—358页。笔者赞成上述观点。这种观点给出了“民法的哲学诠释”这种作为“关于民法的理论”的理论研究的正当性依据。而且,上述法理学和其他法学学科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显然也存在于民法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具体规范的适用这两个领域中各自的思维方式上。所以,本文此处套用了葛洪义教授的相关用语,以便在“法言法语”的层面上对“民法的哲学诠释”这一提法作出进一步的界定。 [8]、[9]参见前引洪汉鼎书,第212、227页。 [10]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11]参见上注书,第二章第三节“哲学诠释学对法治理论的挑战”,第三章第二节“法律诠释的客观性”。在这里,本文在诠释学视角内归结并探讨民法的哲学诠释问题,但这种诠释的合理性标准本身不能由诠释学来提供依据。笔者认为,这并不构成本文在论证上的“断裂”。因为即使在传统诠释学那里,诠释的三要素即理解、解释和应用均被称为技巧,这种技巧与其说是一种遵循规则的方法,毋宁说是一种本身不能由规则保证的判断力,即所谓“规则需要运用,但规则的运用却无规则可循”,因此诠释学与其说是一种人所创造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参见前引洪汉鼎书,第7—8页。所以,即使没有伽达默尔的挑战性理论,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作为具体学科的诠释学(不管是具有何种性质规定的诠释学)为各门具体的人文科学提供各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合理诠释的标准。另一方面,哲学诠释学放弃理解的正确标准的理解,也不可能不否定法律诠释追求相对确定的客观性的努力。否则,法治的秩序、法律的适用、法学的发展就将面临虚无主义的深渊。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应努力构建我们所认可的法律诠释的客观性、合理性的标准。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上述谢晖等所著书的相关章节。 [12]见上注书,第121页。 [13]参见前引葛洪义书,第369—370页。 [14]、[15]参见前引谢晖、陈金钊书,第120页,第113页。 [16]见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第63页,第145页。 [17]参见薛军:《理想与距离》,载于上注徐国栋主编书,第193—199页。 [18]、[19]孙正聿:《简明哲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7页,第201—202页。 [20]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草案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 [21]相关地,徐教授在为其民法典草案的“先人法、后物法”的阐述顺序寻找的一个哲学依据是我国哲学界近年来提出的主体性理论。主体性理论的宗旨是弘扬主体性原则,该原则是客体性原则的对立物。客体性原则从主体之外的客体,从客观事物的特性来说明事物和现象,强调主体在客观事物及其规律面前具有受制约性、受束缚性。徐教授认为,“强调财产关系而忽视人身关系的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贯彻了这一(客体性)原则。”但事实上,财产关系法仍然是从主体的目的、需要出发而作出法律规定的。以财产法的典型——物权法为例,该法并未从作为客体的“物”及其自然规律出发去为“物”立法和为“物”设权,相反,我们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从人(主体)的需要出发而设定物权的。其他的财产法如债法、知识产权法则更不是“强调主体在客体面前的受制约性”的。所以无论其中的人法、物法作何种排序,民法典都是贯彻了从人的目的、需要出发的主体性原则的,与客体性原则无关。 [22]关于文学文本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的国际性讨论,参见[意]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特别是该书的一、二、三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不过,徐教授在近来的论述中指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人法,就是关于主体的法的意思。它本来不须要作任何强调,就是在物法——即关于人与物的关系的法或通过物发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之前的”。见“法律思想网”上的“民法典论坛”中题为“是‘人法—物法’,还是只有一个‘人法’?”的讨论中徐教授(网名andrea)发的帖子。徐教授在这里明确界定了“人法”与“物法”的内涵,并指出民法典要首先规定法律主体,然后再规定具体的法律关系。这无须运用哲学来诠释,在一般的逻辑意义上也很好理解徐教授的这种“先主体,后权义”的民法典编排顺序。不过,按这样的“人法”、“物法”概念来立论,就必须放弃徐教授在其民法典草案中编的层次之设计上采用的“人身关系法”—“财产关系法”这个宏观上显得很“圆润”的结构。对此更为详尽的分析参见薛军《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一文,特别是其中的第三部分。 [23]见前引洪汉鼎书,第228—230页。需注意的是,笔者认为这里关于“完全性前把握”作为理解的一个前提的论述正是对前文所述“应用”是理解的成份的更为具体、深入的说明。理解所筹划的“期待”就是“应用”意图的表现。 [24]参见前引孙正聿书,第33—34页。 [25]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 [26]参见前引洪汉鼎书,第230页。 [27]参见徐国栋《论我国民法典的认识论基础》及《论市民法中的市民》两文。笔者在此之所以不再对这些成功的诠释作出评价,是因为每一成功的诠释就是一次成功的“还原”。相对于文本对实现了不同理论的合理性转化的“还原”的充分表现,其他的评价无异画蛇添足。 |
|
声明:站内文章均仅供个人研究之用,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 前期统计IP计数2320,新计数从2002年4月15日开始运行。 Copyrihgt(c)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