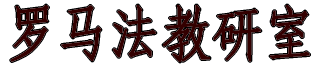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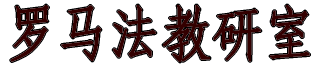

| 本站首页 La prima pagina di questo sito |
罗马法原始文献 Le fonti del diritto romano |
罗马法论文 Articoli del diritto romano |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 Diritto romano e diritto civile moderno |
法律拉丁语 Lingua latina giuridica |
|
|
|
单纯合意即形成债 论罗马债法中的合意主义――从历史的足迹到中国债法之引人注目的演进 费安玲 译 合意(consenso)不仅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传统,而且是现代契约法的基础。人们可以在古老的地中海人民――罗马人的法律中,寻觅到合意主义的诸渊源。该诸渊源孕育了作为债的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完全协商一致[3]。自然,这是历史复杂演进的结果且不总是体现为结构的严密与连贯。在这里,我认为可能的话,可以勾勒出其一些主要的、却绝对是罗马法、中世纪和近现代传统发展中核心性的演进轨迹。 首先作一个解释。拉丁语格言、极为著名的(但是可惜有不少误解)“单纯合意即形成债(solus consensus obligat)”――我将其作为我这篇简短发言的题目――不是罗马人的[4]。可靠的说法是近现代自然法学派思考的结果。事实上,古代法学家们从来没有敢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表达。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形式主义是十分强大的。对于一个远古的、极具特征的社会法律――最为古老的罗马法而言,这一现象是自然的[5]。在罗马,寥寥有限的市民法的债是根据合意而写成和构成的。为了确定我们讨论的主要坐标,值得立即对买卖(l’emptio venditio)、租赁(la locatio-conductio)、合伙(la societas)、委托(il mandatum)的问题进行回顾。在罗马,对于那些通过与形式不符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合意性约定以及在商事习惯中表达的意愿(其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人们在谈论简约行为(pacta atti)时,不仅将合意作为其中心,而且构成了简约的特征,至少是在古代法和(几乎)全部被称为古典法(classico)中是这样,从无效力到产生债的市民法效力[6]。但是,至少是在后古典法时代,罗马债法中的合意有着显著的重要性,这从极为著名的缔约步骤中体现出来,由优士丁尼皇帝的《学说汇纂》流传给后世,在法学家乌尔比安的著作和告示中被探讨[7]。事实上,在乌尔比安的阐述中,其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强调,协议(conventio)是一个一般性的用语,双方当事人在交往中就所有事项达成的协商一致,构成了缔约或和解的原因。[8] 因此,乌尔比安可能是用他的印象主义方式着手研究经院哲学,尽管是列举式,但是显然卓有成效。事实上,正如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同意(convenire)”是集中于并产生在一个唯一点上,也就是这样,由不同的意思表示而形成了合意,即合意于一个“唯一(in unum)”。也就是说,可以用一个后古典时期的注释[9]进行解释,即“形成了统一的意见(giungono ad unico opinione)”[10]。乌尔比安继续分析道:协议(conventio)的概念是引用了公元二世纪的法学家贝狄奥(Pedio)的“时髦”观点,从可以理解的角度或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没有契约即没有包含约束自我的义务,准本体论地说,合意,也可以说是约束(obligatio),是由物(即基于物的转让、基于某物从一方向另一方的让渡)或是由语言(即基于两个口头的意思表示相一致)[11]所构成。甚至,要式口约、典型的口头贸易也是无合意即不产生。总之,没有对债的效力的不同意愿相互碰撞,就不会在法律领域中产生契约之债的效果。 因此,如果没有合意,如果没有当事人的意愿的碰撞,就不会产生契约之债,因而也就不会抽象地产生法律关系构成的资格方式。通过法学家乌尔比安从法律效力的而非是技术问题的考察,这一对罗马人的行为的事实解读被认为是明确的。可能这一考察更要追溯到贝狄奥(Pedio)的学说。我们不知道就这个问题是否还可能涉及更多的古法学家们(这是一个合理的疑问)。 因此,合意主义的问题与罗马债的原始文献有联系。成熟的古典法的制度概念化,被盖尤斯清晰地表达出来。而债的最初的分类是由安东尼时代(公元二世纪)的法学家完成的。在法典编纂中,将债称为不同的债的类型总和,它包括契约所生之债和私犯所生之债。盖尤斯在他的《法学阶梯》第三编“债的论述”的开场白中写道:“现在我们来谈谈债。它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种类:任何的债,或者产生于契约,或者产生于私犯。[12] 首先被研究的是那些产生于契约的债。盖尤斯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四种类型:通过实物形式缔结的契约之债、通过口头形式缔结的契约之债、通过书面形式缔结的契约之债、通过合意形式缔结的契约之债[13]。该划分被解释得十分清晰。这四种契约之债的类型依形式而定,这些形式构成了缔结重要的民事之债的可能。 在古代,缔结契约之债必需的形式是:程式化的语言(i verba)和程式化的文字(scriptura),而盖尤斯则提出了与古代相反的见解:在契约所生之债的内部,种类(genus)反映着法律关系,而法律关系的特征性要素是合意。盖尤斯写道:“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说契约之债是通过合意缔结的,此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语言,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文字,仅需要实施交易行为的人们之间相互同意即足矣(quod nwque verborum neque scripturae ulla
proprietas desideratur, sed sufficit eos,
qui negotium gerunt, consensisse.)”。 显然,我们需要对“合意”作一定义,至少是一般性的定义。自然,合意的范围涉及相互对立的各方当事人的意愿。19世纪伟大的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学说汇纂学派”所谓的“利益法学”概念主义的反对者,提出了他对目的的思考。他认为,实际的终极性目的就是主体提出的所欲达到的目的。我认为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是有教益的。 买卖行为基于各方合意而产生,在探讨买卖行为时,耶林写道:“为了达到其目的,一个人需要与另一方的合作。我的工厂要扩建,就需要我的邻人将其土地转让。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一条路,我就要有获得所有权的可能,是通过购买而获得。在给我的邻居一笔金钱时,其创造了一种利益以实现我的目的。如果我给邻人许多金钱,其数额使得邻人转让该财产所得利益要超过保留该财产所得的利益。如果邻人要求的数额超过了我所能够同意的利益,则我们的利益是不能共存的,取得就没有发生。仅在价格对他而言是相当高(对我而言则相当低)可以产生利益时,对他而言的出售(对我而言是买卖)也就仅在这个时候方达到了两个利益的均衡点,据此,产生了买卖契约的缔结。当认为缔结包括判断缔约双方当事人意图的契约行为时,即达到了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衡平点。这种判断可能是错误的,利益的主观认识或客观情况在其后是可以变更的,但是,应当保持作出决定时的事实,该事实是双方当事人对自己利益进行协商所得出的主观认识,因为其他人不能介入当事人的协商一致之中。契约合意(consensus)中的协商一致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对他们自己利益的完全相容基础上所形成了意愿一致。”[14] 盖尤斯以特殊效力为导引列举道:“买卖、租赁、合伙、委托中的债是通过合意而形成的。(Consensu fiunt obligationes in emptionibus
et venditionibus, locationibus conductionibus,
societatibus, mandatis.)”的确就所有的契约例子而言,通常的要素在这四种契约(准确地说是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中体现出全部特殊的重要性,这些要素渊源于罗马万民法[15]。 盖尤斯在探讨合伙时,经常这样说:“打一个比方说,如果合伙人中某一合伙人的财产被公开或者私下出售,则该合伙解散”[16] 但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合伙,是通过单纯的合意所缔结的合伙(id est quae nudo consensu contrahitur),是万民法范畴内的合伙(iuris gentium est),因此,它是根据自然原因在所有人之间存在着(itaque inter omnes homines naturali ratione
consistit)。按照盖尤斯所阐述的理由,被进行的比较范围非常古老,在该范围内并未区分出所有权(consortium ercto non cito)是“合伙的另类”。合伙的类型之一是罗马市民的合伙,其体现着市民法的古老形式,它变为罗马市民法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其特有的形式,不过,它并不扩展至古老的罗马市民圈子之外。[17] 至于出售作为万民法契约的类型,是保罗所提出[18], 在其对告示进行评论的原始文献中,他写道:“买卖契约属于万民法的范畴,通过合意而实现”。双方当事人合意的本质在买卖契约中似乎体现为一种自然的结果。“万民法”拒绝承认形式主义,双方当事人合意的构成承认不知对民事法律制度的灵活性。因此,“可以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书信或者以传递消息的方式订立契约(et inter absentes contralii potest et per
nuntium et per litteras)”。通过书信表示同意来订立契约的形式,自然与最为古老的要式买卖(mancipatio)毫无关联――这种古老的秤称式的活动主要是有利于交易,同时亦与拟诉弃权(in iure cessio)无关――这种虚假程序适合于财产的转移。 根据保罗的看法,租赁(locazione -conduzione )也突出体现了源于万民法的“自然法则”行为的特征,即“租赁产生于所有民族均共同遵循的自然法则”[19]。在保罗的理论阐述中,排斥了形式的益处(在他的这个片断中,仅明确提示了口头形式)并突出强调了合意,该片断的内容是:“租赁不是以口头形式订立,而是基于合意产生。”[20] 该意思还是通过对买卖的考察得到体现的,保罗明确指出:“如同买卖一样”[21],显而易见,只要有合意,买卖就应当构成,这是一种包含双方当事人同意的行为模式。 与明确的有着特定表达格式的口头表示的需要相反,与物的交付相反,与书面允诺(尤其是有证明的允诺)的效力相反,合意明显地表现出在缺席者之间缔结契约的可能性。这一特征与出现在最古老的市民法中且适用于罗马市民的必须履行的行为模式相比较,具有明显的现代色彩。如果人们能够完全地和直接地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即合意契约的类型在地中海贸易中已经被广泛适用[22],那么,学者们对在交易惯例中出于礼貌接受传播行为的合理性的谴责也是真实的(请注意仅供参考)。万民法所确立的在买卖及其他契约中合意性与强制性并存的制度架构,在古代法学和直至戴克里先皇帝(公元284年-305年在位)之前的一些皇帝谕令中始终保持不变。 扩张主义的罗马经济紧紧地与这些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缔约方式在地中海地区逐渐传播。其扩张至交易、商业,最为古老的市民交易行为表明了其所保护的经济。[23] 买卖存在于一个物与确定的价格之间的交换[24],在缔约的时刻有一个关于缔约的合意,“伴随着人们对价金的商定,买卖即形成”[25],在交易要求被请求迟延时,价金并未被当场支付,直到债在双方当事人形成信任、完全协商一致基础上产生时为止。如同在东方国家的法律中保证金没有作用一样,罗马人的信任(fides)亦没有其地位[26]。 在设立上,租赁与买卖是一样的,我们对此已经进行过说明。盖尤斯写道:“租赁按照类似于(买卖)的规则设立(Locatio autem et conductio similibus regulis
constituitur)”[27]。确定的租金(merces certa)替代了确定的价格,但是规则是相同的。合意支撑着协议,信任则维护着协议。在诉讼中亦同样如此[28]。 合伙与委托是发达经济在法律构成上的另外两个支撑性要素。发达经济是国家宪政改革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共同强化这一改革的结果。但是,不仅仅局限于此。逐渐扩张同时又在缩小的充满活力的地中海地区正在罗马化。 我们现在追忆的上述内容均是缔约方式(在其他领域尚需要进行新的相应的深入研究)通过合意,使得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越来越容易,并且使得在广泛领域内进行的交易越来越安全,它体现出人们所进行的在古老的封闭的古罗马人的世界里所不可想象的纯理论思辨。有关合伙的例证在对奴隶出售中表现了出来[29]。 直至引进格式化程序之前,对于市民之间的争讼(任何一个稍了解罗马法制史演进的人均可以理解),不能想象对合意契约之债(obligationes consensu contractae)的保护。在法律诉讼(legis actiones)严格的形式主义的体制下,实际上并不存在承认对建立于双方当事人单纯合意基础上的法律事实给予保护的诉讼手段。合意契约和强制契约(contratti consensuali e obbligatori)的保护与善意诉讼(bonae fidei iudicia)的传统密切相连。“善意诉讼”是奇特的裁判官在司法活动中确定下来的,大约形成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可能在该世纪最后十年扩展适用于罗马市民之间的关系[30]。 因此,作为国际交往领域中的法律规则,合意契约之债产生于奇特的裁判官司法规则。买卖、租赁、合伙、委托反映了民法法系的形式主义和排他主义的逐渐扩展,它使得在罗马经济中产生深入变革使之不再是牧羊人和农民的乡村经济成为必要,它使得对帝国经济的推动成为必要,同时它使得在新的地理环境与新的不同的世界中将产生罗马政治(和经济)成为必要。关于产生于经验主义实践、从罗马司法中提炼出来的全部规则(有时这些规则远离罗马法律传统),作为“万民法”而被形式体系化[31],并在善意诉讼中存在着“渊源于责任约束与范围的标准”[32]。这些规则现在变成了“罗马人的法律”。公元前198年的执政官塞斯托·埃里奥(Sesto Elio)便已经认识到了对合意买卖的保护问题。在公元二世纪,杰尔苏(Celso)在提起“三分法(Tripertita)”的作者观点时,证明了这点:买受人应当赔偿因其受领迟延(mora in accipiendo)、买卖标的物(如种类物中的一个奴隶)交付中的迟延受领给出售人造成的损失[33]。该情况说明,一些有着前瞻思想的人已经意识到在司法实践中,合意买卖的一些原则显而易见地在经常发生,公元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其他著作中讨论过。[34] 与上述分析有关的是建立在合意基础上的其他契约问题。对我们而言,在没有掌握更多的确认准确年代的可靠资料的情况下,确定这些契约产生的历史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对合意主义现象给予正确全面判断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四种契约把握住了社会和经济的脉搏而成为社会历史共同发展趋势的成果[35]。 罗马法学家们没有对合意的进行多方面的扩展。一个关键点(准确地讲是强调)是合意通过书信或传信人在未出席者之间完成合意的方式[36]。得到法学家们更多认可的形式自由,同样亦有益于监护人许可(auctoritas tutoris)[37]。哑巴亦可以缔结合意契约,当根据他不能表示合意的自然条件而不能参加时,他可以准用要式口约的方式进行[38]。口头契约之债(obligatio verbis contracta)的程式也是D. 45, 1,35, 2所阐述的买卖双方缔约所要遵循的方式,在这个片断中,突出体现出当缺少程式时,如果有合意,则债即被认为成立。其例子就是关于租赁、买卖的多方法律行为。因此,如果在这些契约中的某一契约里,一方没有遵循另一方有关形式的要求,但是,其核心问题是已经协商一致,即双方之间的有着有效的合意。因为这些契约没有被语言而是被合意所确认。故可以说,契约因合意而有效。 此外,通过可信服的事实,行为得被推定出合意[39]。 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合意是构成相互关系的必备要件和充分要件。他在《法学阶梯》下述这一重要片断所写的内容很可能受到东方古希腊的影响:“当人们商定价金时,买卖达成,即使尚未支付价金甚至尚未支付定金;实际上,以定金形式交付钱款的本身就是对买卖已经达成的证明。”[40]法学家盖尤斯描述了罗马人的买卖制度,他从制度构成的角度对合意进行了集中分析。在希腊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制度与现行制度是相对立的,在前者中,双方当事人对物的交换达成协商一致并没有构成契约,至少在原理上,单纯的合意不能产生法律效力;与其说协商一致是由买卖所构成,不如说是由实际效力所构成,交易行为在最大范围内涉及到希腊的各种术语,这些术语反映出买与卖的经济社会的运作[41]。 因此,在罗马法中,合意成为法学家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地中海经济范围内的法律在合意主义和罗马法有关合意契约渊源基础上发展起来,人们通过重新阅读那些在中世纪发现的罗马法原始文献而引起了对该问题的极大注意。因此,中世纪的人们解释为:不能合意将苏格拉底变为石头(Si enim ego et tu consentiamus: puta quod
Socrates sit lapis),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个协议、这个协商一致,从来就不能是合意。[42] 但是,诸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在如下被确定的领域内,尤其是在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的阐述和体系化方面,这些原始文献提供了特有的表示。从格罗萨托里到15世纪的解释者,民法学家的学说在contractus(契约)和pacta(简约)之间保持着对立性的命题。人们在说“pacta vestita(有某种形式的简约,亦称‘穿衣简约’)”和“pacta nuda(物特定形式的简约,亦称‘裸体简约’)”时,甚至在发音(dizione)上保持着与中世纪的对称和谐。只不过前者通过诉权得到了诉讼程序上的保护[43]。 人们还需要考察一下17世纪的自然法学派,因为合意被其提升为债的普遍范畴。在那时,“单纯合意即形成债(solus consensus inducit obligationem)”成为了建立新的契约体系,并最终形成摆脱法定形式约束的统一契约概念的最大可能。这一观念对国际法、尤其是对格罗茨奥(Grozio)和普芬多尔夫(Pufendorf)、对欧洲公法(ius publicum Europaeum)的合约理论有着巨大的影响[44]。包括学院派理论和“学说汇纂”派的理论在内,一个教条主义认识的成熟促使在私法中对合意主义的全面而又系统地接受[45]。意思是“法律行为”成立的核心性决定要素。就契约的其他构成要素而言,在不同的规范中,合意表现出被扩展的独有的效力,至少是有突出它的基本倾向。 的确,在罗马法系(民法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存在着不同,而在有着共同命名的西方法律中采取不同的契约规范也是事实。合意即是如此。在法典化的体系中,契约是其必备的构成且服从于协商一致,契约合意仅在必然产生的强制性效力(如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或者实际效力与(或)强制性效力(如意大利、阿根廷、委内瑞拉、还有法国,提供解释制度解决)时有联系。总之,民法法系的契约缔结在取得合意(consensus ad idem)时已经包含其内。而在英美法系中,合意是契约关系的前提。尽管契约(agreement)最初的效力处于契约关系之外,但是英美法系的契约(agreement)不被认为与大陆法是同一的。 尽管如此,即尽管民法法系的契约表现出更具灵活性的方式,但是两大法系契约模式的基础均渊源于罗马法的合意主义。为此,说到任何一个契约,不能不与今天人们所称的“理性的碰撞(incontro di intelletti; meeting of minds)”相联系,罗马人创造的和在法律上规范的就是所谓的“合意”。 我认为,在广阔的法学研究领域内的中国同仁对这个合意完全可以有着很好的理解与衡量,何况今天的中国法学研究正在快速扩展和深入发展。深刻蕴含着古老而又高尚文明的人类之间和谐传统,使得人们可以在法学方面领域对合意主义的广泛及有益的运用加以研究。“追求善良、顺利、幸福和幸运”我认为正是今天应当倡导的。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法学家和法的历史学家,有幸与法学大家(夸里诺(Guarino)、卡赛尔(Kaser)、德·马尔狄诺(De Martino))共在罗马法的大家庭内。杰出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Rene David)以其聪明才智对中国法律中的世界性的规范与和谐进行了严肃的阐述,在国际政治、法律和经济关系的极为微妙(且是有先见之明的)的时刻,“必要的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最应当讲究的是和解精神,最应寻找的是合意(consensus)。”[46]
() 附录:相关的罗马法原始文献片断: D. 2, 14, 1, 3 乌尔比安:《论告示》第4编 “协议”一词是一个一般性用语,指为取得一致或达成和解而在当事人双方间商定的一切事项。就象我们说“汇合”是指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向同一个地点聚集一样,“汇合”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是指不同的意向变为相同的意向,即达成一致。“协议”一词是广义的,正如贝蒂在他的论述中恰当使用的那样:所有契约,无论是以口头方式设立的还是以要物方式设立的,都必须包含一项协议,否则不产生任何契约关系或债的关系。因此,口头达成的要式口约在缺少合意的情况下亦无效。 盖尤斯著《法学阶梯》第三编 88 现在我们来谈谈债。它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种类:任何的债,或者产生于契约,或者产生于私犯。 盖尤斯著《法学阶梯》第三编89 我们首先看看那些产生于契约的债。这样的债包括四种缔结方式,或者是通过实物,或者是通过语言,或者是通过文字,或者是通过合意。 盖尤斯著《法学阶梯》第三编136 我们说在这些情况下通过合意缔结契约之债是因为: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语言或者文字,只需要实施交易行为的人们相互同意。因此,这种交易也可在未出席者之间缔结,比如通过书信或者传信人;相反,口头契约则不可能在未出席者之间缔结。 盖尤斯著《法学阶梯》第三编135 在买卖、租赁、合伙、委托中的债是通过合意而形成的。 盖尤斯著《法学阶梯》第三编154 同样,如果某个合伙人的财产被公开地或者私下地出售,则合伙解散。但我们现在谈的合伙,即单纯通过合意缔结的合伙,是万民法的合伙,因此它在所有人之间根据自然原因而形成。 D. 18, 1, 1, 2 保罗:《论告示》第33编 买卖契约属于万民法的范畴,通过合意而完成。因此,可以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书信或以传递消息的方式订立。 D. 19, 2, 1 保罗:《论告示》第34编 租赁产生于所有民族都共同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买卖一样,租赁不是以口头方式订立,而是基于合意产生。 D. 45, 1, 35, 2 保罗:《论萨宾》第12编 如果在租赁或者买卖中,一方没有对要约作出回答,但是在其同意被回答的那些事项时,契约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因为这些契约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合意得到确认。 盖尤斯著《法学阶梯》第三编139 当人们商定价金时,买卖达成,即便尚未支付价金甚至尚未给付定金;实际上,以定金名义给付的钱款是对买卖已达成的证明。 [1] 系意大利著名的罗马法学教授,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主席 [2] 再一次感谢我的学生库西莫·卡萧内(Cosimo Cascione)在这篇论文的撰写中所给予的理智的和必不可少的帮助。感谢朋友和同仁、杰出的拉丁语学家焦瓦尼·波拉拉(Giovanni Polara),他的评论性著述给我以冷静。 [3] 参阅:R. Zimmerman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1990. Rist. Oxford 1996) 559. [4] 参阅:M·Talamanca:《Vendita》, in ED. XLVI (Milano 1993 )304. [5]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A·Corbito : II formotalismo negoziale nell’esperienza romano lezioni(Torino 1994) [6] 关于pacta 和contratti直接的关系,请参阅A·Magdelain, Le consesualisme dans l’edit du preteur(Paris 1958) [8] 拉丁文原文是:Conventionis verbum generale est ad omnia pertines, de quibus negotii contrahendi transigendique causa consentiunt qui inter se agunt. [9] 参阅:l’index interpolationum I (Weimar 1929) c: 24, ad h. l [10] 拉丁文原文是:nam sicuti convenire dicuntur qui ex diversis locis in unum locum colliguntur et veniunt, ita et qui ex diversis animi motibus in unum consentiunt, id est in unam sententiam decurrunt. [11] 拉丁文原文是:Adeo autem conventionis nomen generale est, ut eleganter dicat Pedius nullum est contractum, nullum obligationem, quae non habeat in se conventionem, sive re sive verbis fiat. [13] Gaio. 3, 89 [14] 参阅:鲁道夫·冯·耶林著《法的目的》,意大利文本第41页,都灵,1972年版 [15] 参阅:G·格罗索著《罗马契约制度》意大利文本第146页,都灵,1963年版;G. Grosso, il sistema romano dei contratti (Torino 1963) 146; M. Kaser, Jus gentium (Koln- Graz – Wien 1993) 23 ss., 75ss. [16] 参阅:Gaio 3, 154 [17] Cfr. M. Bretone, ‘ Consortium’ e ‘commnio’, in Labeo 6 (1960) 63 ss. [18] D. 18, 1, 1, 2 [19] D. 19, 2, 1 [20] 同上 [21] 同上 [22] 最新的资料:M. Talamenca, ‘ Ius gentium’da Adriano ai Serveri, in La codificazione del diritto dall’antico al moderno (Napoli 1998) 199 s. [23]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L. Labruna , ora in Tradere e altri studii con un saggio di O. Behrends (Napoli 1998)I ss., 79 ss. [24] 在Gai. 3, 140中,盖尤斯写道:“价金应当是确定的。” [25] 参阅:Gai. 3, 139 [26] 关于fides在罗马买卖设立程序中的作用,可以参阅:le illuminanti pagine di G. I. Luzzatto,
L’art 1470 C. C. E la compraendita consensuale
romana, in Riv. Trim. Dir. Proc. Civ. 19
( 1965 ) 926 ss.
[27] 参阅:Gai. 3, 142(意大利原文中注释为Gai. 3, 143,但是有误,译者注。) [28] Si v. Infra. [29] 参阅:Gaio. 3, 148。盖尤斯写道:“我们通常用全部财产或为实施某项行为如出售奴隶而合伙。” [30] 关于这个观点,可以参阅:M. Talamanca, s. v. ‘ Vendita’cit. 305. Cfr., sempre fondamentale, M. Kaser, Das tumische Zivilprosessrechi neu bearb. von K. Hackl (Minchen 1996) 233 ss. [31] 参阅:M. Kaser, Ius genium cit. 23 ss., 75 ss. [32] 参阅:M. Bretone, 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Roma- Bari 1997) 135 [33] 参阅:D. 19, 1, 38, 1 (Celsua 8 dig. ) Si per emptorem steterit, quo minus ei mancipium traderetur, pro cibariis per arbitrium indemnitatem posse servari Sertus Aelius, Drusus dixerunt; quorum et mitri iustissima videtur sententia. [34] Labruna, Plauto, Manilio, Catone: fonti per lo studio dell’empito consensuale?, ora in Adminicula ( Napoli 1995) 179 ss. [35]la lucida impostazine di A. Guarino, Diritto privato romano ( Napoli 1997) 889 ss. [36] 参阅:Gai. 3, 136; D. 44, 7, 2 pr.; I. 3, 22, 2 [37] 参阅: D. 26, 8, 9, 2 [38] Con le opportune, ovvic, cantele, PS. 2,17, 10 [39] 参阅:D. 21, 1, 12 [40] 参阅:Gai. 3, 139 [41] Si v. M. Talamanca; s. v. 《 Vendita’》 cit. 320 s. [42] Cfr. Summa Codicis Azionis Lib. II Rubr. De pactis I; Petrus Placentinus, Summa Codicis Lib. II, tit. III. [43] Sul punto cfr. Per tutti, G. Astuti, s. v. 《Contratto》 cit. 770 ss [44] L. Labruna. ‘Civitas, quae est constitutio populi...’ Osservazioni per una storia delle costituzioni, in Labeo 45 ( 1999 ) 165 ss. [45] G. Astuti, 《Contratto》 cit. 779 s. [46] R. David, I grandi sistemi giuridici contemporanei, ( tr. It. Padova 1980 ) 458 s.; 中文版见勒内·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第485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
|
声明:站内文章均仅供个人研究之用,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 前期统计IP计数2320,新计数从2002年4月15日开始运行。 Copyrihgt(c)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