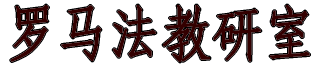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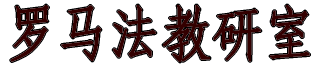

| 本站首页 La prima pagina di questo sito |
罗马法原始文献 Le fonti del diritto romano |
罗马法论文 Articoli del diritto romano |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 Diritto romano e diritto civile moderno |
法律拉丁语 Lingua latina giuridica |
|
|
|
国家何时产生 徐国栋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介绍一种关于国家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国家只是到16世纪才产生。事实上,国家的名词也是在这个世纪产生的。国家的本质在于与其构成成员的人格独立的人格和主权,16世纪才出现了有这些要素的政治实体。在此之前的政治实体如人民、共和国、城邦等,都因缺乏这些因素而不成其为国家。国家之所以后来被理解为一种更早的存在,是黑格尔为了统一德国杜撰国家普遍说的结果,而他的观点又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理论。由于观念交流的自由度的提高,现在我们可以同时欣赏两种国家理论并作出我们自己的选择。 Abstract 国家何时产生?[1] 徐国栋*
在我国,由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统治性影响,国家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观点曾经是这方面的唯一学说。按照这种观点,国家产生的时间很早,就罗马国家而言,它产生在公元前509年的图留斯改革中。这种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构成社会发展5阶段论的基石。但在现代欧洲,存在一种主张国家是16世纪之后的存在的观点,它与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形成对照。为了开阔我们认识国家现象的思路,这种观点值得介绍。 一、国家名实的存在 确实,在原始社会末期,还不存在国家(Stato)一词,迟至16世纪,才由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在其《君主论》的开首部分第一次使用。他写道:“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2]在这一句子中,马基雅维里用“Stato”一词表达“国家”的观念,Stato从Status而来,它最通常的意思是“身份”、“地位”、“情势”、“资格”,[3]现在它显然被赋予与其原有的上述意思甚为不同的意思。马基雅维里之所以把Status改造为“国家”,与乌尔比安的公法定义有关。乌氏在其《法学阶梯》第1卷中(D.1,1,1,2)说:“公法是关系到罗马人的事务之状况的法律”(Publicum ius est quod ad statum rei Romanae spectat)。这里的Status一语,指“一种固定的、稳定的地位,一种以道德上的确定性为基础的秩序的延续性和持久状况的活的标志”。[4]而“罗马人的事务”与下文将要论及的“公共事务”完全是同义词,因为Status rei Romanae 是Status rei publica的不同表达,因此,马基雅维里的Stato,不过是对Status rei publica的简化,是“公共事务之状况”的意思。[5]上述词源考据告诉我们,尽管“国家”一语确实是16世纪作者的创造,但它以古罗马人的政治经验为基础。 马基雅维里在16世纪创造国家一词,并非偶然。在欧洲历史上,16世纪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开始”。[6]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欧洲,各共同体无独立的民族精神,在精神上统一受天主教会的统治;在行政上则处于分裂和割据的状态,各领地、采邑和公国各自为政、闭关自守,形成了中世纪司法管辖权与统治权、帝王的所有权与政治的所有权的二元制,[7]由于缺乏严格的主权观念,领土可随战争或王室成员与贵族的婚嫁而改变。与近代的国家相比,中世纪的国家具有明显的统治者私人所有物的色彩,社会也不具备一个统一社会应有的密切相互关系,而是自给自足生产规模下的分散与疏离。[8]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制度开始解体。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打破了这一地区人民精神上的一统局面,为建立不同的精神地图创造了条件。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区间的联系。领土兼并战争造成了一些较强大的政治中心,出现了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等独立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君权得到了强化,中央权力加强,使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成为可能。[9]与此相应,一切治国的重要手段,如税收、军备、法律等,都有大幅度的改变:人头税变成了永久的税项;建立了常备军;中央性的法院也在频频建立中,所有这些改革,其基本精神都是使一个共同体更趋于集中、统一、有组织性,一句话,更像个国家。作为这种种改革的结果,国家观念形成了,由于其形成,欧洲各国政府间建立起经常的、正规的、永久性的关系,由此开始了外交时代。从16世纪起,欧洲的历史基本上是外交的历史。[10]上述种种现象,史家称之为欧洲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形成,马基雅维里的国家概念,不过反映了这一现实。 如果说马基雅维里的“国家”一词是给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起了一个名字,那么,另一个紧接着他的思想家让·博丹(1530-1596)则揭示了这种形式的本质。 斯人于1576年完成了其《国家论六卷》,他在此书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主权理论,成为这方面理论的奠基人。他从家庭的父权推论出国家的主权,将之界定为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它包括立法权、宣战媾和权、官吏任命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接受服从权、铸币和度量衡定夺权、课税权等8项权力,这些广泛的权力意味着国家的能动活动和重大责任,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国家的现实状况。 主权理论的确立,使国家获得了独立于其成员的属性。在西方语言中,主权(Sovereignty)一词来自君主(Sovereign),表明前者从后者而来,指君主的权力。博丹第一次确立了“国家”与“主权”的联系。在他之后,人们只在国家的意义上使用主权一词。[11]这标志着主权成为国家本身的属性,而与统治国家的人无关。 所以,国家是有独立于其构成分子的人格的人格承担者,这也许是理解国家之本质的一个关键点。最早揭示这一特征的作者是霍布斯,在其《利维坦》中,他按照社会契约论的古老理论描绘了国家(Commomwhealth)的产生。他认为这样的众人授权一个人或集体的行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唯一的人格”。此等人格的承担者就称为主权者,其余的每一个人都是其臣民。[12]看来,国家的产生与法人理论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霍布斯的上述论述,实际上是对社会契约论与法人理论的连接,尽管法人(Juritische Personen)的用语直到1807年才由德国学者海塞第一次使用。 二、黑格尔与国家近代说的对立
由上可知,国家的名称和实质都是近代的现象。而在我国,国家向来被理解为原始社会终结后即存在的现象,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家被作如此理解为呢?这一转变是由黑格尔(1770-1831年)完成的。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已形成强大的民族国家,而黑格尔的祖国却仍然是小邦林立、分裂割据、积弱不振。两种体制,两种结果,这种对比强烈地刺激了黑格尔,为了使自己的祖国现代化,黑格尔力图在理论上把国家偶像化。[13]他把国家说成是一种永恒的现象,人类只有在国家状态下才能过一种伦理的生活,因此,人类始终与国家现象相伴随。[14]他把国家理解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的决定性基础。[15] 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广泛影响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国家的概念来自于黑格尔哲学,把人民看作国民根本上是上个世纪德国文化中的民族概念的伦理特性的果实”。[16]此乃确当之论。 作为其国家普遍说的一种运用,黑格尔还描述了古罗马“国家”的特性。他认为,古罗马“国家”与雅典城邦相比,不是个人的王国,而是个人的具体性从属于抽象的国家的王国。在这里,黑格尔公然把国家现象上推到希腊罗马时代,并表现出一种对雅典国家的赞赏和对罗马国家的贬抑。[17]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黑格尔的门徒,原则上也接受了其老师的国家论。不过,后来他们又受到进化论和摩尔根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否定了国家的永恒性,把国家限定为产生于氏族社会之解体、并且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消亡的现象。尽管如此,相较于国家近代说,马恩仍然把国家的产生时间大大地提前了。具体到古罗马,恩格斯认为公元前509年的塞维鲁斯·图留斯改革造就了罗马国家。这种理论依据的国家标准是与人民相脱离的中央权力的产生和按地域划分居民,与下文将论及的狄骥的国家观别无二致。沿着黑格尔、马恩的国家理论发展,晚近的早期国家理论更把国家的产生追溯到人类历史上更早的时代[18]。无论如何,这些理论都是把近代产生的国家观念投射到古代。 尽管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在这个世界上有巨大影响,但自耶林(1818-1892年)以来的许多作者更为尊重国家观念的发生史。他们认为,国家是一种近代的现象,断言古代世界中存在国家,否认了国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也忽略了古代不存在不考虑其构成而赋予民族以法律人格之现象的事实[19]。这样就产生了“国家近代说”,事实上,它是为了反驳国家普遍说、基于国家的客观发生史建立的理论,在诞生时间上比国家普遍说晚。国家普遍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我国甚为流行;而国家近代说在我国则属于一种陌生的观念,正因如此,需要引进它作为既有的理论的参照系。 国家近代说之所以如此主张,乃因为它对国家有独特的理解。事实上,国家何时产生的问题,换一个角度,就是国家是什么的问题。如果像狄骥那样把国家广义地理解为“任何定居在特定领土上的人的集合,在这样的领土上,强者把自己的意志课加给弱者”[20],那么在任何民族中,这样的国家确实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还不见得会消亡。 但国家近代说把国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实体,它被组织为一个超主体,凌驾于并区别于其构成分子,它有自己的精巧工具和属性,在其自己领土的范围内对其所有的成员实施一种原来是谕令权和君主权性质的法,并且这种法是其实在法的惟一渊源,而国家自身也服从它,国家拥有众多的宪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机关都有预先规定的职权以及专有的和不同的合法性来源”。[21]现代国家的这些属性,古代“国家”显然不具有。 关于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有人还主张,前者可称为“封建军事国家”;后者可称为“民族国家”。后者建立在流动财产(金钱和资本)基础上;而前者建立在土地和地租的基础上。[22]还有人暗示,前者不过是“社会”或“共同体”;后者才是国家。[23] 如果对近代国家的特性还有疑惑,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统一前后的德国、意大利。当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已作为国家崛起在欧洲的时候,这两个民族还在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任人宰割。它们取得统一后,欧洲就有了德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在此之前的德意志和意大利都不是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前后状况的对比,的确可以作为非国家状态与国家状态的对比。 三、古罗马的诸种类国家现象 恩格斯的国家起源说建立在对雅典、罗马、日耳曼3个实例的考察基础上,因此,古罗马的政治经验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有很大影响。重新考察古罗马的诸种类国家现象,对反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乃至历史唯物主义,都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国家近代说,在古罗马,只有人民(Populus)、城邦(Civitas)、共和(Res publica)的概念而无国家的概念。由于国家概念的新近性,许多研究罗马公法的学者不得不把上述三个概念用作国家的含义,造成了一些混乱。 长期以来,罗马学学界有些学者把拉丁文中的Populus当作现代的国家,尤其是蒙森和古列尔漠·诺切拉(Guglielmo Nocera),蒙森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德文中无对应于Populus的词汇。实际上,在拉丁文中,Populus的含义与我们现代人理解的人民的含义不一样,它被用来指称“步兵的队列”或“武装者的集合”[24]。后来演变为指“具体地出席人民大会的人们的集合,这是一种在其自己赋予的组织化的形式中表达其意志的人的集合”。[25]这样的“人民”,就是出席人民大会的全体成员,即全权的公民。尽管“人民”的这种含义已少了许多军事色彩,但它仍不是一个全民的概念,而是“全民”中的具有完全的民事和军事的权利义务者的概念。因此,“人民”并不等于全部人口,不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两者包括在“城邦”的概念中。[26]此外,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概念是抽象的,当我们使用它时,我们不会想到其诸构成成分以及它们的差异所意味的权利义务差异。但拉丁文中的Populus,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会想到它是由平民和贵族、步兵和骑兵等组成的,而这些类别意味着权利义务上的差别,因此,它是一个具体的概念。由于这两点不同,拉丁文的“人民”并不能等于现代的人民,更不能等于现代的国家,因为即使它是现代国家三要素之一的“居民”,还必须补全领土和主权的要素才能构成国家。 那么,我们通常翻译为“国家”的Res publica是否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呢?[27]确实,萨维尼曾经把两者等同。在意大利出版的拉丁文教材中,都把Res publica翻译成“Stato”(国家)。李维的《罗马史》的意大利文本译者,也把所有的Res publica都翻译成“国家”。现代的一种国家形式――共和国――确实由这一拉丁词演化而来。但什么是Res publica?按西塞罗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专著中借西庇阿之口提出的说法:res publica res populi,[28]王焕生先生把这句话译作“国家乃人民之事业”[29];沈叔平、苏力先生将之译作“国家是一个民族的财产”。[30]我以为正确的译法应是“公共事务(共和)即人民的事务”[31]。它说明了“公共”(Publicus)一词由“人民”(Populus)一词而来。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这种公共事务有三种管理办法。第一种是一人之治的王政;第二种是精英之治的贵族制;第三种是众人之治的民主制。西塞罗认为三者各有其长,但把三者的长处结合起来会形成一种最好的统治。西塞罗又说:“如果人民保有其权利,便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好、更自由、更幸福的了,因为他们是法律、审判、战争、和平、缔约、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财富的主人。……只有这样的体制才堪称res publica,即人民的事务”。[32]从上述介绍来看,西塞罗理解的Res publica是政治权力的一种运作方式――在现代被称为“共和”的方式。这种特定的治国之术当然不能与国家本身相等同。 那么,为何现代人把Res publica翻译成“国家”?这是困扰我的大问题。业师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的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的解答是:“这种译法是一种粘贴术,也就是说,把一个不同的概念粘贴在一种现实上,这一本来明确的现实因上述概念而被歪曲”。[33]也许,这种粘贴术是为了解决古代现实与现代概念间的矛盾而运用的。 那么,城邦(Civitas)能否与现代的国家相对应呢?与“人民”和“共和”相较,“城邦”最接近于现代国家,它有包括全体人口在内的“居民”要素、一定领土的要素,但它只有“谕令权”的要素而无主权的要素。前文已述,主权是现代国家本身的属性,而罗马帝国时期的“谕令权”是君主个人的属性。[1]况且,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西塞罗的城邦概念与其人民的概念完全一致,[34][1]“城邦”、“共和”都是“人民”的表象,前者表达的是人民的群体的外貌;后者表达的是人民的利益集团的外观。[35][1]既然城邦缺乏现代国家的主权要素,既然城邦的概念与人民、共和的概念并无本质区别,那么它也不可与现代的国家相等同。 尽管从16世纪才开始有国家的概念,但我们不能排除此前的人类社会具有国家的某些要素。按照卡塔兰诺教授的观点,城邦、共和、帝国、人民等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关系,可用两个相交的圆来表示,两者有共同的地方,但不能等同。如果把现代的国家现象投射到古代,就会像把贝鲁斯科尼的衣服穿在恺撒身上一样好笑。[36] 既然国家如此晚近才存在,那么,为什么许多作者都研究古罗马的宪法呢?1887年,伟大的罗马学学者西奥多·蒙森出版了3卷本的《罗马公法》,由此开创了罗马公私法研究并举的新局面。从1972年到1975年,意大利社会党前总书记、那波里大学教授德·马尔丁诺出版了6卷本的《罗马宪法史》,由此产生了宪法是否必须与国家相伴生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以国家机关为规制对象。卡塔兰诺教授认为宪法可以不与国家相伴生。宪法的概念古今不同。在古罗马,有一些不可废除的规范,可以把它们看作宪法规范。如果把宪法理解为所有的公法和私法的源头,这样的宪法古代是没有的。[37]
四、结论 由于我们受到国家普遍说的深刻熏陶,对国家近代说极为陌生,因此,要我们在两种学说间作出选择,极为困难。但必须注意的是,后者为新说,新说总是在批判旧说的基础上产生的,应该克服了旧说的缺点而更具有解释力。此外,它还是欧洲的通说。由于这两个属性,我对它加以介绍。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熟悉它,坦率地说,我还谈不上吃透了这种理论。正因如此,我在本文中谈论国家近代说,只不过是介绍一种陌生的学说,还谈不上信仰它。必须对国家学说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后,我才能作出理论选择。[38]让我们共同努力来研究这种新理论。如果采用它取代在我国已流行多年的国家普遍说,无异于一场理论革命,会对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法理学原理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两种对立的理论,似乎都以欧洲史作为参照系,很难说它们都能用于解释中国史。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否为国家? 俄罗斯人征服前的远东民族是否为国家? 西班牙人征服的美洲地方是否为国家? [1] 我完成此文后,于2000年10月5-7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第8届中东欧及意大利罗马法学者研讨会期间,向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的皮兰杰罗·卡塔兰诺教授询问了写作本文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他耐心地对我作了有益的解答,特此致谢。 * 厦门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所教授。 [2]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页。 [3] 参见徐国栋:“从身份到契约,从契约到身份”,未刊稿。 [4] Cfr.Guglielmo Nocera,Il binomio pubblico-privato nella storia del diritto,Edizione Scientifiche Italiane,Napoli, 1989,Ristampa in 1992,p.26. [5] Cfr.Fausto Cuocolo, Principi di diritto costituzionale, Giuffrè,Milano,1996, p.17. [6] 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到法国革命》,程远逵、阮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5页。 [7] Ugo Pagallo,BEYOND SOVEREIGNTY,The Problem
of the European Union’s Legal Status in
an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8] 猪口孝:《国家与社会――宏观政治学》,高增杰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年版【】,第9-10页。 [9]参见陈汉文编著:《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10]参见基佐,前引书,第178-183页。 [11]参见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08-318页。 [12]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2页。 [13]参见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4]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254页。 [15] 侯鸿勋:《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16] 关于罗马人的法律思想中没有一种国家观念的依据,Cfr. Pierangelo Catalano, Populus Romanus Quirites, Giappichelli,Torino,1974, p.42. [17] Cfr. Pierangelo Catalano, op.cit.,p.33. [18] 参见H.J.M.克列逊、P.斯卡尔尼克,“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杨玄塞译,载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319页 [19]参见埃尔维拉·门德斯·张:“作为跨民族法适用于罗马与其他民族的随军祭司法”,肖崇明译,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注21。 [20] Cfr. Riccardo Orestano,op.cit., p.187. [21] Ibidem, p.189. [22] 参见亨利·列菲弗尔,前引书,第5-6页。 [23] Cfr. Riccardo Orestano,op.cit.,p.187. [24] Cfr. Pierangelo Catalano, op.cit.,pp.108s. [25] Cfr. Riccardo Orestano,op.cit.,pp.214ss. [26] Cfr. Pierangelo Catalano, op.cit.,p.114. [27] 西塞罗的著作De Re Publica,被王焕生先生将书名翻译成《论共和国》,这本书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同一书名被沈叔平、苏力先生翻译成《国家篇》,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99年出版。 [28] Cfr.Cicerone, Dello Stato, A cura di Anna Resta Barrile, Oscar Mondadori, Bologna,1992,p.38. [29] 前述王焕生先生的译本,第39页。 [30] 前述沈叔平、苏力先生的译本,第34页。 [31]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32] 参见前述王焕生的译本,第45页。 [33] 在1999年10月于北京召开的第二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上对我作出的解答。 [34]Cfr.Guglielmo Nocera,op.cit.,p.18. [35] Ibidem,p26. [36] 卡塔兰诺教授在2000年10月3日解答我的问题时表达的观点。 [37] 同上。 [38] 我在“奎里蒂法研究”一文(载《第二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9年)中,还采取了早期国家理论。在这篇论文中,似乎又转向了国家近代说,也许这是对国家现象之认识深化的结果。我不愿受到朝秦暮楚的批评,因此我强调,在本文中,我只是介绍国家近代说。我个人关于国家的观点,须等待进一步的研究后才能形成。 |
|
声明:站内文章均仅供个人研究之用,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 Copyrihgt(c)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