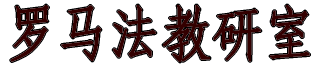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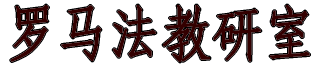

| 本站首页 La prima pagina di questo sito |
罗马法原始文献 Le fonti del diritto romano |
罗马法论文 Articoli del diritto romano |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 Diritto romano e diritto civile moderno |
法律拉丁语 Lingua latina giuridica |
|
|
|
对盖尤斯《法学阶梯》第二编第29片断的解读 2002级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曾健龙 盖尤斯《法学阶梯》第二编第29片断(以下简称为Gaius.2,29)说道:“Sed 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 in iure cedi
possunt; rusticorum vero etiam mancipari
possunt.”黄风先生将其译为:“但是,城市土地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转让;乡村土地权也可以通过要式买卖转让。”[1]译文中的“城市土地权”之相应拉丁文为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iura之意为“权”,即所谓“城市土地权”为对于praedium urbanum的权利。“乡村土地权”中的“乡村”的原文则为rusticum。这里似乎体现出了一种有趣的“城乡差别”。由于盖尤斯《法学阶梯》中没有对于城市土地权和乡村土地权的具体解释,我进一步查阅了中国和美国的两部权威法学词典,却产生了一个疑问。 一、词义分析。 元照英美法词典中对于praedium urbanum的解释是:“<拉>(罗马法)非农用土地 用于居住或商业的土地,也可指建造在城市或乡村,供人们居住和使用的大小建筑物”;元照英美法词典并收有praedium rusticum的词条,其释义为:“<拉>(罗马法)乡间田产;乡间不动产 主要指乡村土地。但在泛指非住宅用地,如田地、草地、果园、花园、树林等时,也可以是位于城市内的这种用地。”1999年第7版的Black’s Law Dictionary中对praedium urbanum的解释是:“[Latin] An estate used for business or for
dwelling; any estate other than a praedium rusticum.”对praedium rusticum的解释是:“[Latin] An estate used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1979年版第五版的Black’s Law Dictionary中对于praedium urbanum词条的解释里更明确地指出是不是praedium urbanum并非按地理位置处于城市或乡村而定:“In the civil law, a building or edifice intended
for the habitation and use of man, whether
built in cities or in the country.”按照这两部权威词典的释义,关键的区分倒不在于城乡地理位置之别,而是要看其用途了。 问题于是出来了:Gaius.2,29中的praedium urbanum是否包括了乡村的建筑物?与之对应的“乡村土地权”是否包括了城市的非建筑用地? 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中一段关于优士丁尼时代物的基本分类的叙述是支持上述两部词典的区分的:“不动物包括土地或地产(它们分为城市的和乡村的,即建筑物和田野);其他物则为可动物。这种划分在古典法中几乎不存在”[2]。根据这段论述,我们可以作如下对比:
可见,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合理的猜测: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对实践会产生重大区别)的区分,如果在优士丁尼时代和盖尤斯时代有重要的差异的话,优士丁尼很可能会有所说明(如优士丁尼提到的“要式转移物与略式转移物的区分太古老,同样应予以废除。”[3])。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二卷第3题“地役权”第1段中说道:“对都市不动产的权利,是固着于建筑物之上的役权,之所以被说成是对都市不动产的权利,乃因为所有的建筑物,即使它们被建造于乡间,都被叫做都市不动产。”(I.2.3.1中“对都市不动产的役权”的相应拉丁文是praediorum urbanorum servitutes)[4]类似内容的说明是盖尤斯《法学阶梯》中所没有的(但是,要考虑到现存盖尤斯《法学阶梯》内容不全),那么,优士丁尼的这段论述会是暗示和盖尤斯的不同么?很可惜,不是这样的。下面这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对于盖尤斯而言,对城市地役权的解释和优士丁尼的对都市不动产的地役权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学说汇纂》中引用了盖尤斯《行省告示评注》第7卷中的一段论述:“城市地役权有:建筑物加高役权、禁止建筑物加高役权、妨碍邻居采光役权、将滴水排向或禁止将滴水排向邻居房顶或地上的役权及将支梁插于邻居墙上的役权,最后还有建造伸出物、遮盖物及与此类似的其他物的役权。”(D.8,2,2)[5]显然,盖尤斯的“城市地役权”是针对建筑物的,与地理位置处于城市或乡村无关。 D.8,2,2这个线索使我查阅了学说汇纂的拉丁文本,在D.8,2,2中城市地役权的原文是urbanorum praediorum iura,和盖尤斯《法学阶梯》中的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的区别仅在于词序而已,虽然不懂拉丁文,但似乎可以推知二者含义相同。那么,是黄风先生翻译错了吗? Gaius.2,29中的“城市土地权”和“乡村土地权”其实就是“城市地役权”和“乡村地役权”吗? 再看了盖尤斯《法学阶梯》的另外两个片断后,我发现还不能就此结案: Gaius.2,14a:“……城市土地的役权(servitutes praediorum urbanorum)是略式物。” Gaius.2,17:“因而,几乎所有的无形物都是略式的,乡村土地的役权(servitutes praediorum rusticorum)除外。实际上后者显然是要式物,虽然它们属于无形物。” 再看Gaius.2,29:“但是城市土地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转让;乡村土地权也可以通过要式买卖转让。”总结这三个片断如下表:
既然Gaius.2,29中的城市土地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转让”,如果Gaius.2,29中的城市土地权就是地役权,Gaius.2,14a中把城市土地的役权定性为略式物似乎就显得很怪异了。 那么,Gaius.2,14a中的“城市土地的役权”(servitutes praediorum urbanorum)、D.8,2,2(同样是盖尤斯的论述)中的“城市地役权”(urbanorum praediorum iura)、优士丁尼I.2.3.1中的“对都市不动产的役权”(praediorum urbanorum servitutes)三者是一回事固然已无疑问,但上表的对照却暗示了Gaius.2,29中的“城市土地权”(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很可能是另一回事——同样是盖尤斯的论述,D.8,2,2中的urbanorum praediorum iura和Gaius.2,29中的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虽然只是同样三个拉丁词的不同排列,但其含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分析到这里,我们面对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如果Gaius.2,29中的城市土地权就是地役权,那么Gaius.2,29中的城乡区别就是非农业用地(建筑物)/农业用地的区别;如果Gaius.2,29中的城市土地权不是地役权,那么我们得先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除了对相应拉丁文的对照方法(前面对其的运用已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之外,我们也许还可以通过另一条分析进路来解决这个谜:从盖尤斯《法学阶梯》中的相关论述来作体系分析。 二、体系分析。 为了这个目的,先将相关片断摘录如下: Gaius.2,14:无形物是那些不能触摸的物品,它们体现为某种权利,……实际上,继承权、用益权和债权本身都是无形的。对城市土地和乡村土地的权利(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 et rusticorum)同样属于无形物。 Gaius.2,14a:物有些是要式的,有些是略式的。……城市土地的役权(servitutes praediorum urbanorum)是略式物。 Gaius.2,17:几乎所有的无形物都是略式的,乡村土地的役权(servitutibus praediorum rusticorum)除外。实际上后者显然是要式物,虽然它们属于无形物。 Gaius.2,22:要式物则是通过要式买卖向他人转让的物品;所以它们被称为要式物。有关要式买卖的说法同样适用于拟诉弃权。 Gaius.2,27:意大利土地是要式物,行省土地是略式物。 Gaius.2,28:无形物显然不能接受让渡。 Gaius.2,29:但是,城市土地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转让;乡村土地权也可以通过要式买卖转让。 Gaius.2,30:用益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的方式设立。实际上,用益物所有主可以通过拟诉弃权向他人转让用益权,使该人拥有用益权并且自己保留赤裸所有权。至于用益权人,通过拟诉弃权向用益物所有主转让用益权,将使用益权与自己相脱离并且与所有权相合并;而在通过拟诉弃权向他人转让用益权的情况下,该权利则仍然为他所保留,因为人们实际上认为这种转让无任何效力。 Gaius.2,31:但是,这显然适用于意大利土地,因为这种土地可以通过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转让。至于行省土地,如果某人想针对它设立用益权、各种通行权、饮水权、建筑物加高权、防止遮挡邻居采光的限制加高权或者其他的类似权利,他可能通过简约和要式口约的方式设立,因为对于这些土地不能适用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 Gaius.2,32:但是,由于用益权可以针对人和其他动物而设立,我们应当认为在行省也可以通过拟诉弃权设立这种用益权。 Gaius.2,33:我们说用益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的方式设立,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人们也可以采用以下方式通过要式买卖设立用益权:在转让所有权时可以扣除用益权;在这种情况下,用益权实际上并未被买卖;而是在对所有权进行买卖时被加以扣除,从而使得一人享有用益权,另一人享有所有权。 现在,可以进行我们的体系分析了。 1、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可能的指称。Gaius.2,29的上下文中涉及对于praedium的权利包括三种:所有权、用益权、地役权。那么,永佃权和地上权呢?彭梵得说道:永佃权和地上权,在结构、历史发展以及给罗马法的物权制度带来的变化方面,是很相似的制度。它们两者的出现要比役权、用益权等被优士丁尼归进役权范围的类似制度晚得多;它们两者在“市民法”中都没有规定,也未被古典学说明确承认为物权[6]。那么,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可能指对土地的所有权、用益权、地役权之任意一种或任意几种的总和。 2、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是无形物。理由有二:第一,其措辞和Gaius.2,14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完全相同,而Gaius.2,14明明白白地说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是无形物;第二,Gaius.2,29是紧接着讨论无形物的Gaius.2,28后作“但是”的讨论的。 3、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不应该是指土地所有权。理由是:Gaius.2,13明确说土地是有形物。作有形物和无形物的区分的用处在于几乎所有无形物都是略式的(Gaius.2,17),如果把土地等有形物的所有权也认为是无形物,那么有形物和无形物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了。转让土地和转让土地所有权是一回事,若强要说前者是转让有形物而后者是转让无形物,则未免有无益地玩弄辞藻之嫌,务实的罗马法学家当不至为此。既然如本文上一段分析2所言,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是无形物,那就不该包括土地所有权。 另一个可以佐证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不是指所有权的证据是Cfr. Matteo Marrone提供的:所有权(Proprietas)是一个在共和晚期才产生的概念,在此之前,人们为了指明物的所属,说这个物是我的或张三的就行了。为了强调是一种合法取得的权力并为最古的法所承认,人们加上“依奎里蒂法”一语。例如说,“依奎里蒂法这个物是我的(Hanc rem meam esse aio ex iure Quiritium)”。可以说,所有权现象内蕴在名词的所有格和物主形容词的语言现象中。有了“我的”,就有了“你的”,这两个词就成了所有的社会冲突的根源。到了共和晚期,出现了“依奎里蒂法的主人(Dominus)”的表达,指所有人。更晚的时候,才出现了Proprietas一语,它来自“自己的”(Proprius)一词,抽象化为“所有权”。因此,所有权就是“自己之物”的意思。但“依奎里蒂法的主人”一语并未消亡,而是与所有权的概念并行使用。在古典时代和后古典时代的许多《民法大全》的文本中,还有用“主人”的,但“依奎里蒂法的”一语被优士丁尼取消掉了(C.7,31,1pr)。[7]Gaius.2,20、Gaius.2,22、Gaius.2,30、Gaius.2,33……等片断中指称“所有主”或“所有权”时的语法现象均验证了Cfr. Matteo Marrone的说法。可见,在盖尤斯时代,对praedium的所有权是不会用iura praediorum来表达的。 那么,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会是用益权吗?对用益权的说明紧跟着Gaius.2,29,如果二者是一回事,倒也是符合盖尤斯《法学阶梯》的论述风格的。我们不妨就先假设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是用益权。 为了除去这一假设可能产生的Gaius.2,29和Gaius.2,30之间的两个矛盾,需要先澄清两个问题: A.Gaius.2,29中的用益权转让和Gaius.2,30最后一句否定用益权转让(“在通过拟诉弃权向他人转让用益权的情况下,该权利则仍然为他所保留,因为人们实际上认为这种转让无任何效力”)之间存在的矛盾无法调和。对这个矛盾的解决是:黄风先生对Gaius.2,29中“转让”的翻译可能有错,其对应拉丁文中并无带转让之意的词,possunt只是“可能”或“可以”,这可能指“转让”也可能指“设立”。换言之,如果Gaius.2,29中确指“转让”而非“设立”,那么Gaius.2,29中的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就不可能是用益权。我们为了假设Gaius.2,29中的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是用益权,就必须同时假设Gaius.2,29中规定的是关于权利的设立而非权利的转让。 B.Gaius.2,30中所谓的“用益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的方式设立”之意在于说明用益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的方式为他人设立,并不排斥通过要式买卖的方式在出卖物时同时为自己设立用益权(Gaius.2,33)。这样,我们又消除了假设中的Gaius.2,29中的用益权设立两种方式和Gaius.2,30中第一句话的矛盾。 接着,我们引入意大利土地和行省土地的区别。 首先,Gaius.2,29中所作的城乡区分不能适用于行省土地的用益权问题(Gaius.2,31中明确行省土地用益权可以通过简约和要式口约的方式设立,而Gaius.2,29中只允许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两种方式)。 那么,Gaius.2,29只可能适用于意大利土地。Gaius.2,30和Gaius.2,33规定在意大利土地上设立用益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和要式买卖两种方式,而Gaius.2,29中也只允许拟诉弃权和要式买卖两种方式。乍一看二者并不矛盾,细端详才发现有问题——把二者结合起来,会产生很奇怪的推论(且不论Gaius.2,29中的城乡是按地理位置区分还是按用途区分): A.若Gaius.2,30和Gaius.2,33适用于所有意大利土地(不论“城乡”),则Gaius.2,29的规定是与之矛盾的,所以, B.城市土地的用益权不能通过要式买卖的方式为自己设立(而乡村土地的用益权可以),这显然是取消了用益权设立的一种合理方式,这很难让人理解其中有何合理理由。而此一重要的区分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不直接说明而通过如此迂回的手段(简直胜似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来表达(对用益权的设立和转让方面的论述片断之前后文并无缺失),与盖尤斯的整体论述风格可谓格格不入。 小结。若Gaius.2,29指的是用益权,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Gaius.2,29中并不是关于权利“转让”的规定而是关于“设立”的规定;2、Gaius.2,29的规定只适用于意大利土地;3、城市土地的用益权不能通过要式买卖的方式为自己设立(而乡村土地的用益权可以)。 相反地,支持Gaius.2,29指的不是用益权的观点却可以有如下支持: A.如前述,意大利城市土地的用益权不能通过要式买卖的方式为自己设立,这颇不合理。就算真相确实如此,对于这一重要区分,在Gaius.2,31和Gaius.2,33中并无任何说明(从Gaius.2,29到Gaius.2,34之间并不存在现存本不完整的情形),这极不符合盖尤斯的论述风格。 B.前述分析2中提到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和Gaius.2,14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的措辞完全相同,这暗示了其指称可能完全相同。而在Gaius.2,14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和继承权、用益权、债权是并列的。与现代民法不同,在罗马法中,地役权并不属于用益权,如果Gaius.2,14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是地役权,那么,其和继承权、用益权、债权并列就完全合理。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第4点分析结论: 4、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不太可能是指用益权。 5、那么,Gaius.2,29中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应该还是指地役权喽?如果希望回答是肯定的,还得解释两个问题: A、地役权的“转让”是可怪的,因为它应该固着于需役地之上,这一点是古代罗马法学家所确知的。黄风先生在其《罗马私法导论》中也明确地说道:“地役权的设立是为需役地服务的,因此,它随着需役地所有主的变更而自动地向新的所有主转移;供役地的所有主不能因需役地所有主的变化而撤销役权,不能单独地转让役权,也不能针对役权设立役权”[8]。这个问题容易解释:黄风先生可能译错了。前文提到,在Gaius.2,29的拉丁文中并无“转让”之词。所以,Gaius.2,29完全可能是在讨论地役权的设立方式。 B、我们需要说明下面这个表格是合理的:
在说明之前,首先也要澄清两个问题: (1)Gaius.2,29只适用于意大利土地,不适用于行省土地(从Gaius.2,31可知)。这不会成为我们解释的难题:行省土地既然被认为是价值上不如意大利土地的略式物,对其地役权的要求也就不需要那么严格了。 (2)盖尤斯眼中的城市地役权和乡村地役权是按照是否是对于建筑物的地役权而区分的。这一点前文已经确定地论证了。 接着我们对上面的表格进行解释: (1)为什么城市地役权是略式物而乡村地役权是要式物? 梅因和彭梵得都正确地告诉我们,在古罗马,对物的基本区分的标准是这种物对于社会的重要程度。[9]再对比一下城市地役权和乡村地役权的内容: 《学说汇纂》中引用了盖尤斯《行省告示评注》第7卷中的一段论述:城市地役权有:建筑物加高役权、禁止建筑物加高役权、妨碍邻居采光役权、将滴水排向或禁止将滴水排向邻居房顶或地上的役权及将支梁插于邻居墙上的役权,最后还有建造伸出物、遮盖物及与此类似的其他物的役权。(D.8,2,2)[10] 同样在《学说汇纂》中,时代比盖尤斯晚不了几十年的乌尔比安认为[11]:乡村地役权有:个人通行权、运输通行权、道路通行权和引水权(D.8,3,1,pr)。乡村地役权还应包括:汲水权、饮畜权、放牧权、烧制石灰权及采掘泥沙权(D.8,3,1,1)。同样,可以创设将耕地放牧于邻地的役权(D.8,3,3,pr)……(乌尔比安还讨论了几种不太重要的乡村地役权,不再援引) 很明显,城市地役权是略式物而乡村地役权是要式物是合理的。 (2)为什么意大利的城市地役权就算是略式物也不能采用简约或要式口约设立? 这是因为盖尤斯时代的法是认为行省土地是较不具有价值的,意大利的土地是要式物,而行省土地是略式物(Gaius.2,27)。对于意大利土地来说,和土地密切相关的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地役权的设立、用益权的设立都不能采取略式物的方式(哪怕这种权利本身可能被划归略式物)。 (3)为什么乡村地役权的设立可以通过要式买卖的方式而城市地役权不可以(只能用拟诉弃权)?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可能从对罗马法发展进程的揣测中获得。周枏说道:“罗马最早产生的役权是耕作地役……田野地役先于城市地役而产生,其目的是便用于农村的耕作。而罗马毁于兵灾后,在重建时才有建筑地役的产生,故建筑地役即称为城市地役。”[12]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由于乡村地役权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相较于城市地役权所代表的社会关系而言更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这使得乡村地役权更早地进入了法律的视野,并逐渐将其作为一种对世权来看待。这种对世性使得人们可以象看待物一样地看待它,由此可以在要式买卖(曼兮帕蓄)中对它实行“让渡”。这种曼兮帕蓄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乡村地役权在人们心目中的“物性”。在盖尤斯的时代,城市地役权还不能象乡村地役权在人们心中具有那么强烈的“物性”,便只得通过拟诉弃权的方式获得设立——既然不是有形物,自然不好让渡,而曼兮帕蓄的最根本特色就在于对物的让渡。若真实的历史果如上述猜测,那么,乡村地役权和城市地役权在设立方式上的区别(Gaius.2,29)只是历史的遗迹而非特意人为的区分。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区别并没有带来实践上的太大不便,而法律的延续惯性便占了上风。我们现代人或许会认为这样的区分从抽象的逻辑上看并不合理,但是,古罗马人并不为此烦心——他们是务实主义者。 彭梵得的一段论述佐证了我的最终结论是正确的:“设立役权的行为,在古典法中,是明示的和要式的行为。对于生者间行为来说,必须通过要式买卖或拟诉弃权以取得‘要式役权’,即乡村役权,为取得城市役权、用益权等当时不包括在役权范围内的类似权利,则需实行拟诉弃权。让渡被明确宣布为不允许的。对于行省土地,罗马市民不能在法律上取得役权,就象他们对它不拥有市民法上的所有权一样。为了以某种方式建立这种关系,所有主可以采用简约商定一方将对另一方的土地行使役权,这种简约应由双方加以确认并通过要式口约加以保证;这样当所有主对其债务负责的继承人提起诉讼时,人们即可以此来保护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设立的役权也从裁判官那里获得了真正的物权保护。”[13]另一个佐证是黄风先生自己提供的,他在2002年出版的《罗马法词典》中对iura praediorum的解释是:“地役权(见servitutes praediorum)”[14]。 最后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既然Gaius.2,29中的iura praediorum和Gaius.2,14a中的servitutes praediorum是一回事,盖尤斯为什么用两种说法?按笔者的猜测,可能的理由有两个,不妨分别称为“区分决定说”和“体系排除说”: 其一,区分决定说。所有权和用益权都是不作“城乡区别”的,作“城乡区别”的对不动产的权利仅地役权一家,那么在Gaius.2,29的文本脉络中用iura praediorum来指称servitutes praediorum也就并无不妥了。 其二,体系排除说。前文述及,对盖尤斯来说,对praedium的物权(对世权)不外乎所有权、地役权、用益权三种。iura praediorum既是对于城市不动产的权利(也就是无形物),就不可能指对不动产的所有权,而用益权又有了专门的概念(涉及用益权的相关片断中,其拉丁文的字根皆相同:Gaius.2.14中的ususfructus、Gaius.2.30中的ususfructus、usumfructum、usumfructuarius、Gaius.2.31中的usumfructum、Gaius.2.32中的ususfructus、Gaius.2.33中usumfructum)来指称,那么iura praediorum就只可能指地役权(不要忘记盖尤斯时代还不承认地上权和永佃权是物权)。盖尤斯既觉得毫无引起歧义之可能,也就可以将iura praediorum和servitutes praediorum替换着使用了。 至此,含糊的地方都已澄清,看似矛盾的地方也都被解释得不矛盾了,真相已然大白:Gaius.2,29中的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就是城市地役权。黄风先生译错了,Gaius.2,29的准确译文是:“但是,城市地役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设立;乡村地役权也可以通过要式买卖设立。”如果要严格地以“信”而非“达”作为第一要旨,也可翻译为“但是,城市土地权只能通过拟诉弃权设立;乡村土地权也可以通过要式买卖设立。”但加个译注说明这“城市土地权”和“乡村土地权”其实就是指“城市地役权”和“乡村地役权”会更好些。此外,我们知道,这里的“城乡区别”不是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同时,Gaius.2,29只适用于意大利土地。 三、几点启示。 Gaius.2,29所讨论的城市地役权和乡村地役权在设立方式上的区别到优士丁尼时代已被废除,对此后的法律发展也不再产生过影响。那么,本文所作的分析,是否只是“汉儒穷经”式的努力呢?笔者以为不尽然。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可以在对法律和法律概念的认识方面获得一些启示——或曰本文的分析和结论提供了对一些观念的验证。 启示1、对法律发展的认识。 法律从来就不可能是完全静止的,它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演进,罗马法当然也不例外。法律演进的历史常常会在法律中留下残迹——不论这残迹在新的情况下是否仍有必要。但当历史的残迹已构成对新的需求的阻碍时,也就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Gaius.2,29验证了这一法律演进的观念:Gaius.2,29对城市地役权和乡村地役权在设立方式上的区别,验证了历史发展的残迹;而这一区别在后世的消逝,则验证了历史残迹的湮灭,成为罗马法交易严格形式主义由盛而衰发展历程的见证。 启示2、对法律概念的认识。 根据本文的结论,盖尤斯在Gaius.2,29中用iura praediorum来指称servitutes praediorum,这一“史实”是大可玩味的——从中我们可以验证一些关于法律概念的观念,并由此认可这些深刻的观念早已潜藏于罗马法学家的头脑中了。 前文曾述及盖尤斯用不同概念指称同一事物可能有的两个理由,先从第一个可能的理由——区分决定说——说起。 根据区分决定说,盖尤斯能用iura praediorum指称servitutes praediorum,是因为在前后文的脉络中有urbanum和rusticum之分。换言之,盖尤斯实际上是以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来指称servitutes praediorum urbanorum。我们可以把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作为一个比iura praediorum多了一层限制的概念(但仍是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何以能为人所理解或有效呢?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东荪认为:命题和概念之间并无鸿沟的隔离,概念苟加以分析都可以化为命题。而一切概念没有不可分析的,除了特别情形下的基本假定不在其列。例如“孔子”这一概念就可以化作“在周末有一个学者叫作孔子”。[15]准此,概念是否具有意义、概念是否可以理解、概念是否有效,莫不依赖于其背后蕴涵的命题是否有意义、是否可以理解、是否有效。再进者,我们对概念的理解经常建立在对事物分类的理解之上。例如:对“男人”这一概念的理解建立在理解“人分男女”之上。可再举例明之:“美味的糕点”之可解,在于糕点可以区分为美味的和非美味的这隐含一命题可解;而“美味的物权”之不可解,在于物权可以区分为美味的和非美味的这一隐含命题毫无意义。 既已说明概念和命题的关系,则可进一步考察理解命题时必须考虑的两个问题:其一,命题是否可解,受限于理解者的知识范围。如“机架式服务器”这一概念可解,是因为其隐含的命题服务器可分为机架式和非机架式两种是可解的。但对于计算机了解不深的人可能对这一命题不能理解,从而不能理解“机架式服务器”的概念。由此,要理解盖尤斯的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对盖尤斯时代法律知识了解太少是不行的。其二,我们知道,概念可以区分为描述性命题和规范性命题,这种区分背后其实是描述性命题和规范性命题的区分。男人是描述性概念,因为人分男女是描述性命题,这种命题可辨别真伪;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是规范性概念,因为地役权区分为城市地役权和乡村地役权是规范性命题,这种命题无所谓真伪,却可区分是否有效。iura praediorum urbanorum被解为城市地役权,是因为这个概念是有效的(Gaius.2,29中说明了有设立方式上不同的规定呢),而若将其解为所有权或用益权,则这个概念就无效了(Gaius.2,29中设立方式上不同的规定若适用于所有权或用益权会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也不可解——对于盖尤斯时代的读者来说,因为他们对于所有权和用益权明明不曾作“城乡区别”。那么,我们从本文的分析和结论中,可以验证:对法律概念的把握,是不可能先于对此概念背后的命题的理解的,毋宁说,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和对其背后的命题的理解是浑然一体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盖尤斯在Gaius.2,29中用iura praediorum来指称servitutes praediorum的另一种解释——体系排除说。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其一、如前文所述,在盖尤斯《法学阶梯》中,指称用益权的概念极为统一。而对地役权的表达情况则不然,如Gaius.2,14a中使用servitutes praediorum(D.8,2,2中盖尤斯使用praediorum iura),这是概括方式,而在Gaius.2,31并列讨论“用益权、各种通行权、饮水权、建筑物加高权、防止遮挡邻居采光的限制加高权或者其他的类似权利”,这是列举方式。用益权和地役权在概念统一程度上的差异强化了我们认为iura praediorum不是用益权的信心,也生动地展示了:法律概念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概念的名称、内涵、外延逐渐明确化,不同法律概念明确化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其二、体系排除说的要点在于,从用语上说,iura praediorum既不可能指所有权(参见前文引用Cfr. Matteo Marrone的论述),也不太可能指用益权(参见前文对“用益权”用语统一性的分析),再结合当时的物权(对世权)仅所有权、用益权、地役权三类这一背景,则iura praediorum应指地役权。依此,则盖尤斯的心中,已有物权(对世权)体系性的整体认识了。桑得罗·斯奇巴尼在为黄风先生译盖尤斯《法学阶梯》写的前言中强调了盖尤斯“为在系统论述中形成内在的体系做出伟大的努力”,他指的是盖尤斯的人、物、诉讼三分体系。[16]我们发现,除了斯奇巴尼说的大体系外,盖尤斯还有物权的小体系呢。从这个小体系里,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后世物权种类法定主义的种子!或许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先假设有一个封闭的物权体系,里面共有三种物权,然后根据iura praediorum不是另外两种而推出其为第三种,最后再依此而推出有一个封闭的物权体系(里面共有三种物权)。对此诘难,笔者预作答辩:当时的物权体系中共有三种物权,这不是笔者假设的,而是疏理了盖尤斯《法学阶梯》第二编中所讨论过的物权之后归纳而得。所以,这一论证的出发点是自立的。由此可以根据iura praediorum不是所有权或用益权而推出其为地役权。再由盖尤斯“胆敢”凭借排除法(排除法必然依赖封闭的体系)而用iura praediorum指称servitutes praediorum而不虞引起歧义,来推出盖尤斯心中有一封闭的物权种类体系。这确乎不是循环论证。 如果体系排除说成立,那么,我们得到的启示便是,Gaius.2,29验证了法律概念对于体系的依赖。准此,对法律概念的理解,也就不能脱离于对其背后更大的体系的理解。毋宁说,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和对其背后体系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正如其和对法律概念背后命题的理解之间的关系一样,是浑然一体的。 [1] 本文有关盖尤斯《法学阶梯》中的引文均出自:(古罗马)盖尤斯著,黄风译:《法学阶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意】彼得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192页。 [3] 【意】斯奇巴尼编,范怀俊译:《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2页。 [4]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第138~139页。 [5] 【意】斯奇巴尼编,范怀俊译:《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150页。 [6] 【意】彼得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264页。 [7] Cfr. Matteo Marrone, 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 Palumbo, [8] 黄风:《罗马私法导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4—225页。 [9] 参见:【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7-159页;【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190~191页。 [10] 【意】斯奇巴尼编,范怀俊译:《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150页。 [11] 【意】斯奇巴尼编,范怀俊译:《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150~151页。 [12] 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90页,393页。 [13] 【意】彼得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260页。 [14] 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15]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16] (古罗马)盖尤斯著,黄风译:《法学阶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2页。 |
|||||||||||||||||||||||||||||
|
声明:站内文章均仅供个人研究之用,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 Copyrihgt(c)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